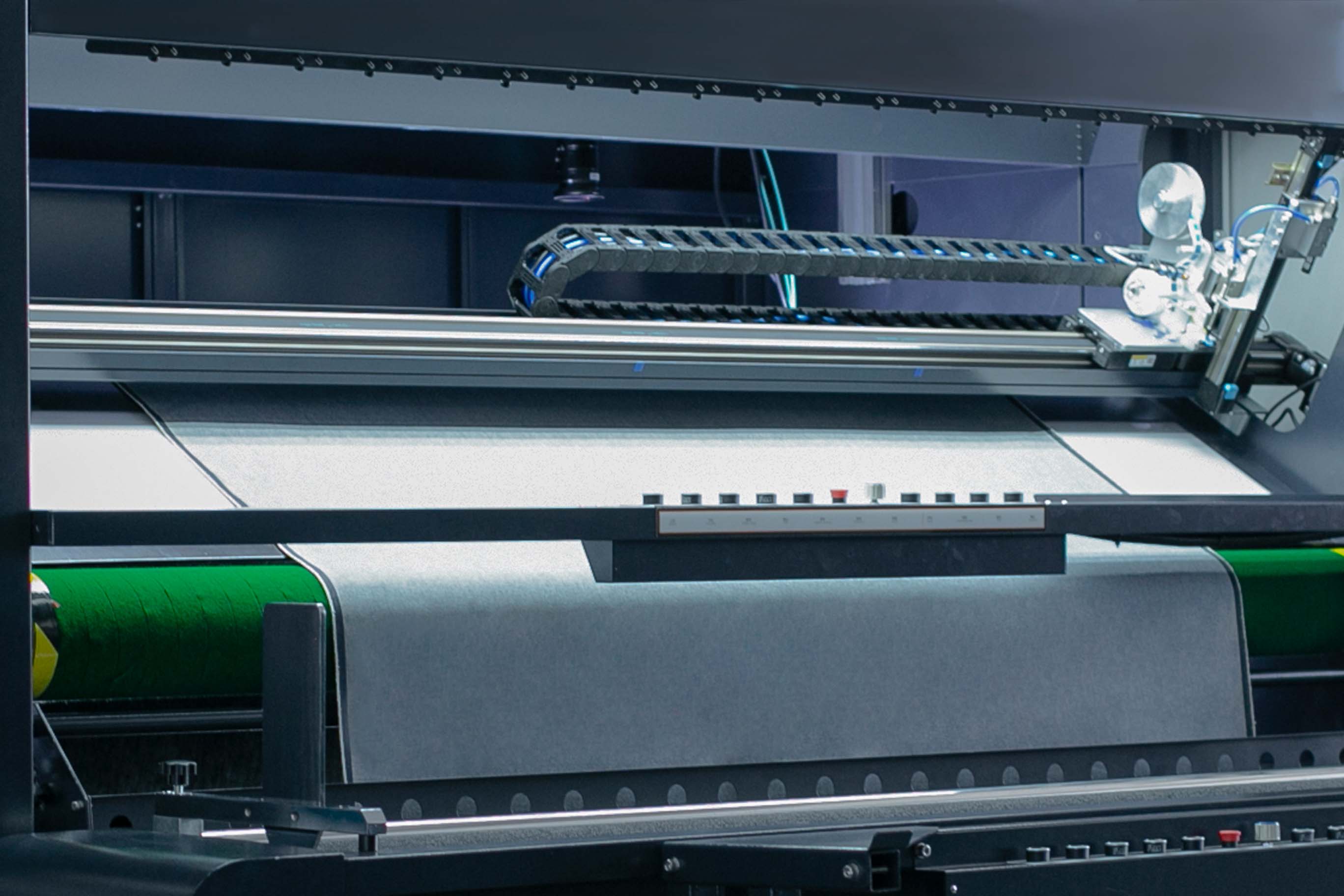潮涌时的掌舵人
晨雾还没褪尽时,中交三航局六公司罗屿13-15号泊位项目的沉箱已在晨光里泛出冷光。雾气像一层薄纱裹着海面,远处的海岸线朦胧不清,唯有沉箱硬朗的轮廓在微光中愈发清晰,静静等候着新一天的施工指令。
时间回到项目攻坚最吃紧的那段日子,海风裹着咸湿的水汽,日夜不停地扑打在这座孤悬海外的岛屿上。
“沉箱CX-10测位移数据再核一遍!”测量员王龙滨蹲在临时搭建的料棚下对着对讲机喊道,用擦镜布擦去全站仪镜头上的海雾,镜片里映出的,是这座孤悬海外的码头岛屿——我们要在这里建起3个泊位,让700米海岸线长成新的港堤。
航道里,船影叠着船影。随着工程推进,港口建设进入高峰期,现场十多条船像被塞进玻璃瓶的鱼,挤在有限的海域里。
让这些船只在拥挤航道内井然有序、各司其职的,是调度室里的船长杨志。
五十多岁的人,背有点驼,总穿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袖口磨出毛边。他的调度台像个小型战场,海图铺得满满当当,上面用红笔圈着潮位线、用蓝笔标着船舶坐标,铅笔头削得尖尖的,总在“涨潮1.2米”“落潮0.8米”的数字旁画圈。老杨干这行近三十年,调度过的船只比谁都多,大伙儿都说:“只要老杨在调度室坐着,再乱的场面也能给捋顺了。”
最忙的是基槽挖泥和沉箱安装交叉施工那段时间。挖泥船刚把基槽清出来,抛石船就得紧跟着抛填基床,打夯船要瞅准潮水稳的时候把基床夯实,拖轮、起重船和半潜驳还得见缝插针地运沉箱、装沉箱,一环扣着一环,半点耽误不得。
那天清晨,杨志盯着调度屏上密密麻麻的船舶坐标,眉头拧成个疙瘩。“挖泥3号,往东挪五十米,给整平船腾作业区!”“返航的泥驳,等沉箱过去再过航道!”“抛石3号船原地作业,小心船浪。”他对着对讲机语速飞快,手指在海图上圈出一个个作业区域。
突然,对讲机里传来:“调度调度,整平船1号锚可能被卡住了,目前收不回来!”只见在海图上整平船的位置正好挡住了沉箱运输的航道。杨志盯着海图,手指敲着桌面,此刻所有的船只、周围的地形地貌还有潮水的涨落情况都在他的脑中交织。
片刻后他拿起对讲机:“整平1号船,不动!拖轮转东偏南15°,等抛石3号船收锚移动完成后通过!锚艇去B3区帮抛石3号船起锚,争取在落潮前让出备用航道!”他话音刚落,调度屏上的船舶图标开始重新移动,像一盘迅速归位的棋子。
当拖轮带着半潜驳从新的航道进入安装区域时,第一缕阳光刚好照在调度室的玻璃窗上,杨志揉了揉发酸的眼睛,发现海图上被汗水洇出的晕圈里,“沉箱安装11件”的字迹依然清晰。
这样的日子重复了一百多个。站在护岸上回望,远处依稀可见的跨海大桥像条银带,将岛屿与大陆连在一起,而如今,安装完成的沉箱和抛填完成的隔堤一同将海面划分开来,划出填海造陆的界限,同时也是新码头的前沿线。杨志掏出那本磨破的记录本,翻到第一页,上面是刚上岛时写的:“今日,挖第一方淤,船舶调度3艘。”再往后,是密密麻麻的船名、时间、作业坐标。
海风掀起他的衣角,露出胳膊上被晒出的黑白交界线,那是日光与工作服袖口反复较劲的痕迹。“你看这岛,你再看看这艘半潜驳,”他指着远处的三航工8,“当初这里就是一座小岛,后来慢慢的桥造了起来,再后来岛上的泊位跟着填筑出来,到现在,马上咱们新建的3个泊位也很快完成了。咱这辈子的成就,不就像这码头?一锤一凿,一土一石,慢慢就立起来了。”
暮色里,甲板上的灯次第亮起,照得海面碎金般闪烁。我忽然懂了,所谓奋斗,从不是惊天动地的伟大壮举,也不是趋之若鹜的谋取名利,而是沉箱安装时的零误差定位,是记录本上洇着汗渍的笔迹,是把蓝图上的线条一寸寸化成港口的筋骨。就像那古语说的,合抱之木的根,原是一粒种子在泥土里的执着,九层之台的基,本是一捧黄土在岁月里的坚守。
而我们,就在这岛与海之间,做着那粒种子、那捧黄土,在礁石里扎下深根,让荒岛长出拥抱世界的臂膀。
(杨伟胜 张雨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