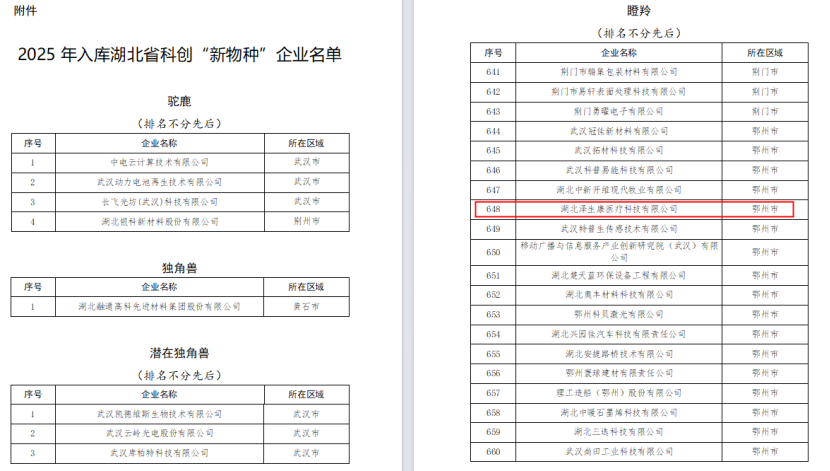建功高原的热血情怀
从福建宁德到西藏札达,这不仅是一段跨越万里的旅程,更是一场灵魂深处的跃迁。
刚下飞机,我深吸了一口气,干燥而稀薄的空气让我瞬间头晕目眩、心跳加快。身边不少旅客带着氧气瓶,我也感到身体不适,但我知道:前方,还有更远的路等着我。

从拉萨到札达,要坐两个多小时的飞机,再坐5个小时的大巴,翻越海拔5000多米的雪山垭口,一路上荒无人烟,雪线如白蛇般盘绕山间。最终来到札达——祖国最西部的一隅,也是我的挂职之地。
作出赴西藏挂职的决定,并不容易。
那天,父亲正在接受手术,我守在医院的走廊里,手机响起,是单位打来的电话。母亲望着手术室的方向,轻轻说了一句:“你去吧,家里会好的。”我点头应下,却也明白,从那一刻起,我将踏上另一条人生轨道,把沉甸甸的责任留给至亲,带着组织的信任和殷切的期盼去往雪域高原。

我来自福建宁德,一座靠海的城市,山海相拥,四季温润。我曾在宁德边检站工作,那些日子虽忙碌,却有家的烟火;也曾主动报名到广西三江支教,在那里我见到了另一种“偏远”——孩子们坐摩托车翻山越岭上学,家长风里雨里接送,孩子眼中闪着对知识的渴望。那时的教室虽已修缮一新,但教育资源仍极为匮乏。一位年长的教师从未接触过英语,三尺讲台上靠一台卡式录音机,教孩子们反复跟读单词“apple”,那份执着和清贫中的坚守,触动了我内心最柔软的角落。
或许正是那时起,我便在心里种下了一颗“走出去”的种子。恰逢高原在召唤,我愿意出发。
札达,位于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的西藏阿里地区,是全国人口最少的县之一。这里空气稀薄,气候干燥,但风中摇曳着美丽的格桑花。刚来时,我常头痛恶心,夜里睡不踏实,白天走几步就喘。之后便只有“静”——不是城市的安静,而是一种真正的空旷与辽远:没有霓虹、没有喧嚣,天地之间,仿佛只剩自己。
就在这片广袤沉寂的大地上,驻守着一群年轻的移民管理警察。他们就像深植雪原的藏红花,在静默中傲然挺立。
我下乡驻点的萨让边境派出所,没有营房,没有快递。萨让边境派出所所长曾说:“我们巡边连路都没有,是大家一步步踏出来的,有的无法通车,只能骑马,有的甚至只能一人经过,旁边就是悬崖峭壁。”民警住在临时板房中,冬夜冷得像刀割。有人说,这里是“来了不想走,走了不想来”的地方。

有一次,我随民警入户宣传,步行几公里山路才抵达一户牧民家。老人耳背,汉语也不太标准,民警一字一句耐心解释居住登记政策,直到老人露出明朗的笑容。那天阳光很好,我们围坐在帐篷外喝酥油茶,远处雪山巍峨,近处草地泛绿。我忽然觉得,这就是“团结”最真实的模样——是一次次语言不通却坚持沟通的努力,是一次次真心换来的信任。
在楚鲁松杰边境派出所,我见证了风雪中的“逆行者”。一次,一辆车在海拔5800米的相让拉达坂侧翻。空气稀薄到一句话都说不完整,民警却在风中排查隐患、配合随车吊精准操作,硬是将车从冰冷的沟里拖了出来。还有一次,大雪突至,一辆私家车陷入积雪无法动弹。那晚,民警顶风冒雪,拿铁锹一铲一铲清雪,徒手推车,直到凌晨 2 时,最终将群众安全送下山。
“在这么荒的地方,没有你们,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临别时,车主的话让我久久难忘。那一刻,我真切理解了“戍边警察”4个字背后的意义:不仅是守边者,更是风雪中的

“摆渡人”,是高原上最温暖的依靠。
负责宣传工作后,我开始尝试用镜头和文字记录这些温情时刻。慢慢地,从最初的无人问津,到如今每月数十篇稿件被各级媒体采用,札达边境管理大队的宣传工作正一步步迈上新台阶。我们用照片记录下雪夜巡逻的背影,用视频展现民警与牧民间的深情,用文章讲述一桩桩小事背后的守护与担当。这些故事不为掌声,只愿让更多人知道:在高原之巅,有人默默替我们负重前行。
我也代表大队参加了札达县的演讲比赛。讲述这些故事时,台下很多听众红了眼眶。比赛结束后,有人问我:“你后悔来西藏挂职吗?”我微笑回答:“不后悔,相较于长期戍边的你们,我的挂职不值一提。”

其实,札达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神秘,也没有电影里那样轰轰烈烈的剧情。这里真实、粗犷,有时让人落泪,有时让人沉思。但正是这样一个地方,让我变得更加坚定与沉静。
札达,也在一点一滴地改变着。边境线上铺起了水泥路,边民住进了安居房,孩子们用双语朗读课文。风还是刺骨的风,但风中,多了欢笑的声音。
我从不觉得自己是英雄。我只是把故乡的山海情怀,带到了风雪高原;把一颗平凡的心,放在了祖国边境这块热土上。
如今,我已逐渐适应这里的节奏。依旧会巡逻、入户、拍摄、写稿,也依旧会想念海边的家。但每当站在边境线上,脚下是祖国的土地,背后是万家灯火,我便知道,我来对了。
札达,藏语意为“下游有草的地方”。这片草原不富饶,风沙常在,空气稀薄。但这里有信仰,有坚守,有中国人的热血情怀,有属于这个时代的温度。
我还有一年的挂职时间,故事仍在继续,脚步依旧未停。而我愿意,继续走在“去有草的地方”的路上。
免责声明:市场有风险,选择需谨慎!此文仅供参考,不作买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