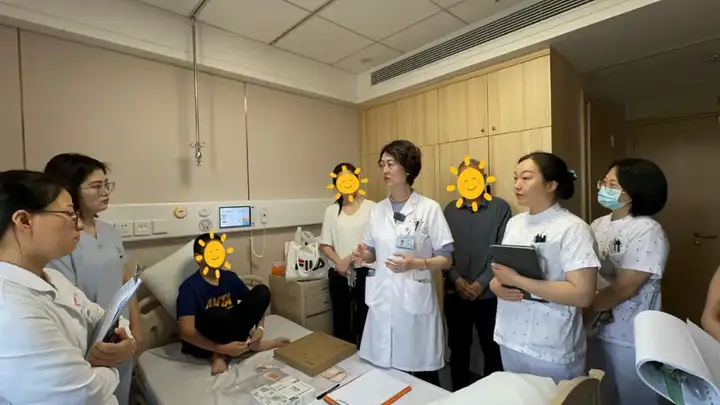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慢煮生活》读书心得体会
《慢煮生活》是汪曾祺的散文集。草木有情,美食有味,落笔故人,品味人间。他用朴素简单的笔触,勾勒花鸟虫鱼,描画大好河山。既写回忆中的美食,也写乡土民俗,平凡小事。
汪老先生不喜欢“君子远包厨”这句话,他喜欢做菜,更喜欢在小说中用大量的笔墨记录美食,翻动书页仿佛徐徐展开了一幅散发浓浓烟火气的画卷:是《葡萄月令》中,人们为种好葡萄而忙忙碌碌喷洒波尔多液吧;是《夏天》中,泡在井水里冰冰凉的西瓜和栀子花香吧;抑或是《切脍》中那薄如纸的鱼肉……我从未去过江苏高邮,但我却记得吃高邮咸蛋要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扎下去,就冒红油,蛋黄是通红的。还有他家乡的咸菜茨菇汤,红烧野鸭子,凉拌荠菜。我从未去过云南,但我却记得云南的干巴菌中吃不中看,但“收拾干净了,撕成蟹腿状的小片,加青辣椒同炒”“入口细嚼,半天说不出话来。在他的充满烟火气的文字下,我能感受到的,是他对生活的表白。
而最让人难以忘怀的,是他对生活的热爱。
汪曾祺将对花鸟虫鱼、一草一木的怜爱,都融入他的作品中。我特别喜欢的是他在作品中体现的一种不畏困难疼痛、积极向上的生活哲学。那是遭受过身体上的病痛后,照样活得简单纯粹,热爱生活的潇洒。著名作家冯唐评价他的文章说:“明末小品式的文字,阅读时开窗就能闻见江南的荷香”。他的作品没有任何多余的字词,也没有华丽的辞藻点缀,行文处处透露着朴实与自然,诉诸直觉,忠于生活。将自己的情感与万物融合,真真做到了万物有情。他说:"爱,是一件非专业的事情,不是本事,不是能力,不是技术,不是商品,不是演出,是花木那样的生长,有一份对光阴和季节的钟情和执着。一定要爱着点什么。它让我们变得坚韧、宽容、充盈。业余的爱着。"他说:“世界先爱了我,我便不能不爱她。"谈他在览泰山后的感受:"在山上呆了七天,我对名山大川、伟大人物的偏激情绪有所平息。同时我也更清楚地认识到我的微小,我的平常,更进一步安于微小,安于平常。”
看过了汪曾祺先生关于吃食方面的书,也看过了梁实秋先生的《雅舍谈吃》,他们都属于榜上有名的“大吃货”,不仅懂吃,会吃,还经常写吃,风格同是属于“闲适小品寄寓人生意趣”的平淡,但我感觉汪曾祺先生的文字似乎更易抚慰人心,汪曾祺先生出生于一个小康家庭,写作的食物多是“下里巴人”式的贫农食品,并且带有更鲜明的地方特色,这样,汪曾祺先生写饮食自然就和许多地方的风俗、民情连在了一起;而梁实秋先生出生于一个中产阶级,家中自有厨娘为他烹饪美食,他懂吃、会吃,但极少做吃,且其写的多是“阳春白雪”式的美食。这就导致了汪曾祺的文字对于大多数平民阶层来说有了更多的代入感和参与感。
读汪曾祺的小说时,能感受到他确实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作者在创作时,在叙述语言上要尽量冷静,不要带很多感情色彩,尽量说得平平淡淡,好像作者完全无动于衷。越是好像无动于衷,才能使读者感觉出作家其实是有很深的感触的。”
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唯有热爱,可抵岁月漫长。我极喜欢他在《人间草木》扉页上写得那句话“如果你来访我,我不在,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它们很温暖,我注视它们很多很多日子了。”我们应像汪老一样,"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若可偷得浮生半日闲,捧一晚人间烟火 ,赏一回日出日落,倒也不枉此生。(吴泽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