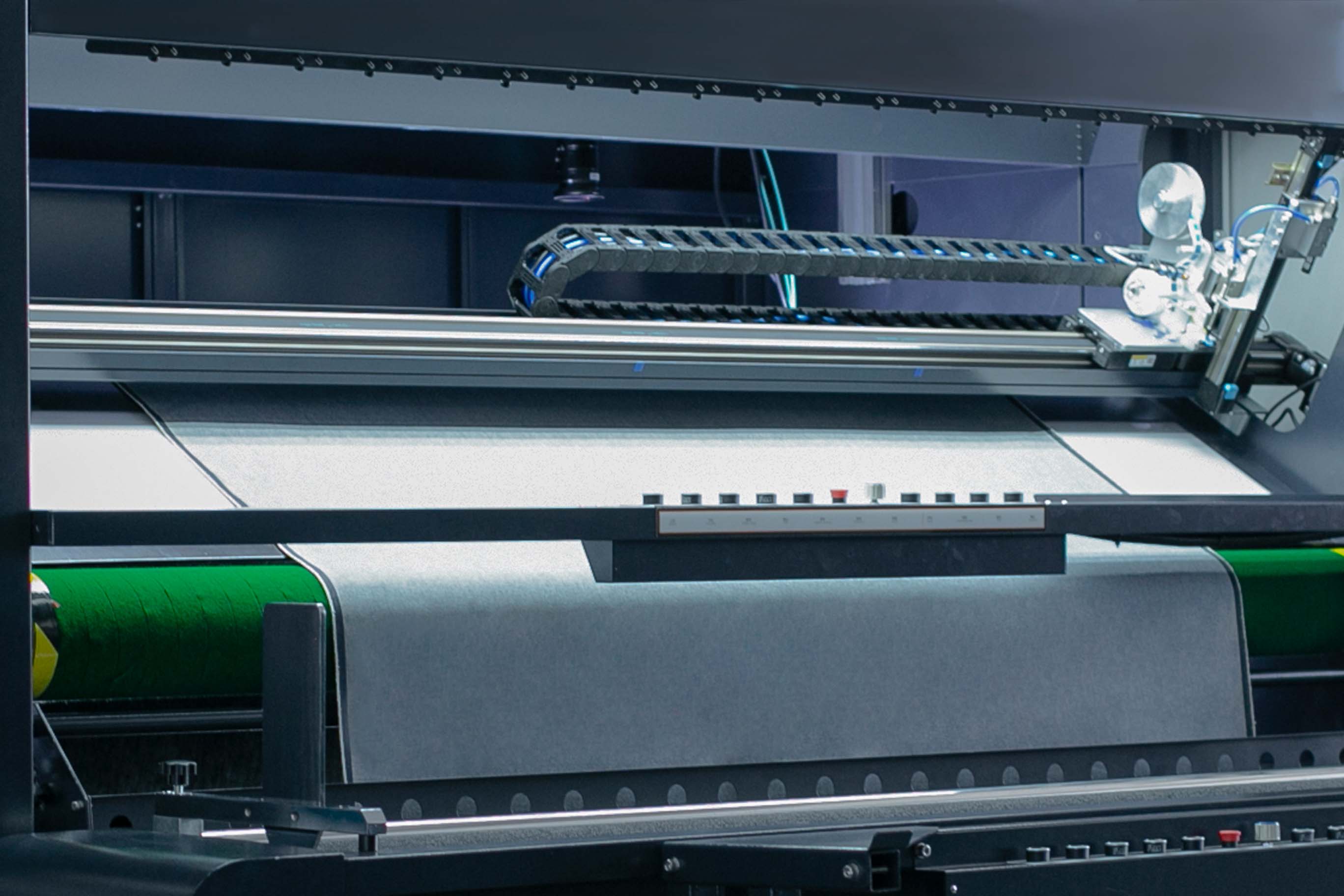孔达达:中国文物流失海外的历史脉络探源
中国文物流失海外是一个跨越千年的复杂历史现象,其规模之大、渠道之多元,构成了全球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独特景观。笔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中国文物学会统计数据为基础,结合历史档案与政策文献,对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进行全面量化分析梳理。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总数保守估计超过3000万件,其中博物馆馆藏约167万件,民间收藏则十余倍于此。在传统的海外贸易、战争掠夺、非法走私等认知之外,新中国成立初期至改革开放前的政策性文物出口创汇构成了数量最为庞大的流失渠道,这一时期通过官方渠道出口的文物数量巨大,深刻塑造了海外中国文物收藏的格局。我们系统梳理了文物流失的四条主要途径,评估了各途径的相对规模与历史背景,并基于近年文物追索实践,探讨流失文物回归的法律框架、现实挑战与未来路径。研究发现,文物追索工作虽取得显著进展,但已回归文物仅占流失总量极小比例,实现系统性回归仍需国际共识、法律创新与多方协作的持续努力。
文物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物质载体与历史记忆的凝结。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拥有着璀璨夺目、延绵不绝的物质文化遗产。然而,除郑和下西洋、丝绸之路的国际贸易之后,特别自19世纪中叶以来,大量中国文物因各种原因流散海外,成为全球博物馆与私人收藏中的珍品。这一过程不仅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屈辱与苦难,也反映了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迁以及不同时期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碰撞。
长期以来,公众对文物流失的认知多聚焦于战争劫掠与非法走私,如圆明园之痛、敦煌遗珍之殇。然而,历史的复杂性远非如此简单。通过最新统计数据与档案材料,揭示了一个长期被忽视却规模巨大的流失渠道,20世纪50至80年代,为支援国家经济建设,通过官方外贸体系进行的文物出口。这一发现促使我们必须以更全面、辩证的视角审视文物流失这一历史课题。
通过调研显示,一整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文物学会等权威机构的调查数据,对流失海外中国文物的总量、等级与地理分布进行精确量化描述。二突破传统认知框架,系统分析文物流失的四条主要历史渠道,尤其深入剖析“文物出口创汇”这一特殊历史现象的政策背景、实施规模与长期影响。三结合近年成功追索案例,评估文物回归的现实路径、法律障碍与未来趋势,为构建更加公正、有效的文化遗产国际治理体系提供学术参考。
首先了解流失海外中国文物的总量、等级与分布,基于数据的宏观图景,要理解中国文物流失问题的全貌,必须首先建立可靠的数据认知基础。尽管全球范围内的精确统计面临巨大困难,但多个权威机构的调查与估算,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触目惊心却又相对清晰的图景。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一项不完全统计,在全球47个国家的218家博物馆中,馆藏的中国文物数量达到167万件。这一数字本身已极为庞大,足以填满数十座大型博物馆。然而,这仅仅是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同一调查指出,流散在海外民间的中国文物数量,约为博物馆馆藏的十余倍之多。据此推算,海外民间收藏的中国文物可能超过2500余万件。
中国文物学会的统计提供了另一重要参照,该学会指出,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有超过1000万件中国文物流失到欧美、日本和东南亚等国家及地区。上海大学学者段勇的研究则估计,海外公共机构和私人收藏的中国文物总量超过1500万件。综合这些数据,并结合文物贸易历史分析,学术界普遍接受的一个保守估算,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总数超过3000万件。这一数量,远超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文物总量,相当于将一部厚重的中华物质文明史搬移到了海外。
主要数据概览
全球博物馆馆藏:约167万件
海外民间收藏估算:超过2500万件
中国文物学会统计(1840年后):超过1000万件
本文采用的保守总量估计:超过3000万件
流失文物的价值不仅体现在数量上,更体现在其无可替代的历史、艺术与科学价值。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在流失海外的文物中,属于国家一、二级文物的珍贵品超过100万件。这意味着,每十件流失文物中就有一件是具备重大价值的国之重器。它们包括:青铜重器:如西周丰邢叔簋、曾伯克父青铜组器等,承载着铭文与礼制信息。书画珍品:如东晋顾恺之(传)《女史箴图》唐代摹本,现藏于大英博物馆,却在20世纪初被错误地“肢解”装裱,造成了不可逆的损伤。石窟珍宝:从天龙山石窟、龙门石窟被盗凿的佛首、浮雕,到广胜寺等处的壁画,这些文物脱离原境,其艺术与宗教内涵大打折扣。宫廷秘藏:圆明园兽首、汉白玉石柱等,是近代中国屈辱历史的直接见证。
从地理分布看,流失文物的聚集地与近代以来的国际政治经济中心高度重合。
英国:大英博物馆是收藏中国文物最著名的海外机构之一,藏有约2.3万件,其中不乏《女史箴图》、敦煌绢画等顶级珍品。
法国:吉美博物馆、枫丹白露宫等收藏了大量来自圆明园等处的文物。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弗利尔美术馆、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等均以系统的中国艺术收藏闻名。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京都国立博物馆等收藏了大量中国古代艺术精品,其中不少与近代战争有关。
民间收藏流通网络:除博物馆外,大量文物沉淀于全球私人藏家、基金会、画廊和拍卖行手中。伦敦、纽约、香港、巴黎等地是主要的中国文物交易中心,文物在此不断流通、转手,其踪迹更难追踪。
文物流失并非单一原因造成,而是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条件下,通过多种渠道发生的复杂过程。传统叙事多强调战争掠夺与盗掘走私,这固然重要,却不足以解释总数高达数千万件的流失规模。笔者研究系统梳理出四条主要路径,并尝试对其相对规模与历史逻辑进行辨析。
路径一:古代及近代的商贸与文化交流(和平流出),这是时间跨度最长、性质最为复杂的一类。自丝绸之路开启以来,中国的丝绸、瓷器、漆器、茶叶等便作为商品,源源不断地输出到中亚、西亚乃至欧洲。郑和下西洋时期,瓷器、钱币等也被作为礼物赠与沿途国家。这些物品在当时属于贸易品或礼品,其流出是古代正常国际交流的一部分。明清时期,通过广州等口岸,大量外销瓷、外销画定制生产并销往欧洲,满足了西方社会的“中国风”趣味。
这类文物通常具有明确的外销属性,其工艺、纹饰可能融合海外需求。它们构成了海外中国文物收藏的早期基础,且其所有权转移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具有合法性或合理性。学者段勇指出,海外中国文物中大部分是通过正当贸易、馈赠等合法途径获得的商品或艺术品。这部分文物虽然数量庞大,但并非通常意义上引发情感痛楚与追索诉求的“流失文物”。
路径二:战争劫掠与殖民掠夺(暴力流失),这是最刺痛民族记忆、最具道德争议的流失途径,主要集中在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上半叶,与中国的百年屈辱史紧密相连。其特点是系统性、暴力性与非法性。
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对“万园之园”圆明园进行了骇人听闻的抢掠与焚毁。无数宫廷珍宝被作为“战利品”运往欧洲,至今散落在英法各大博物馆与私人手中。2023年从挪威回归的7根圆明园汉白玉石柱,便是这场劫掠的见证。
甲午战争(1894-1895年)后,日本开始有组织地从中国攫取文物。如用户提到的辽宁三学寺石狮被移往靖国神社,即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八国联军侵华(1900-1901年):联军在北京等地公开劫掠,皇宫、衙署、王府、寺庙无一幸免。《永乐大典》副本残本、天文仪器、佛教法器、书画典籍等被大量掠走。大英博物馆所藏《女史箴图》即由一名英军军官在此期间从颐和园盗出。
日本侵华战争(1931-1945年):日本在占领区进行了有计划、大规模的文物调查与掠夺,从东北的“鸿胪井刻石”,到华北的石窟造像,再到华东的图书馆珍藏,损失无法估量。
通过此途径流失的文物,往往等级极高、来源清晰、承载着沉重的民族创伤。它们是文物追索中道德与舆论压力最大的部分,也是国际社会关于“殖民遗产”归还讨论的核心对象。
路径三:近现代的盗掘、盗窃与走私(非法流失),当社会动荡或监管乏力时,针对地下文物与馆藏文物的犯罪活动便异常猖獗,形成文物流失的“黑色通道”。这一途径贯穿整个20世纪,并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达到高峰。
盗墓路经:疯狂的盗墓与遗址盗掘,盗墓者使用炸药等粗暴工具,只为快速获取可流通的陪葬品,对墓葬结构和历史信息造成毁灭性破坏,许多具有关键历史价值的文物(如刻有“中国”字样的汉代铜镜)就此消失或损毁。出土文物随后通过复杂的走私网络,经香港、澳门等地中转至国际市场。
馆藏流失:馆藏文物监守自盗与外部盗窃。如广州美术学院图书馆原馆长萧元,利用职务之便用赝品调包143幅馆藏名家书画,其中125幅被其拍卖,造成巨额损失。
国际贩运网络:被盗文物通过洗钱、伪造(流传记录)等方式,在国际艺术品市场被“洗白”,最终以“合法”身份进入拍卖行或博物馆。2007年意大利查获的796件套中国文物,以及2024年美国返还的38件藏传佛教文物,均是各国海关或警方截获的走私赃物。
此途径具有隐蔽性、犯罪性、持续性和高破坏性。虽然单次规模可能不如战争掠夺,但长期累积数量巨大,且因其非法性质,是当前国际执法合作与司法追索的重点对象。
路径四:特殊历史时期的政策性出口创汇,这是在既往公众讨论中常被忽视,但在数量上可能构成海外中国文物存量主体的流失途径。它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初期(约1950年代至1980年代) 这一特定历史阶段。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外汇储备极度匮乏。在工业品、农产品出口能力有限的条件下,文物被视作一种特殊的“战略资源”和“出口商品”,承担起为国家工业化积累宝贵外汇资金的重任。这并非随意决策,而是一套有组织、有规划的国家行为。
1960年,文化部与对外贸易部联合颁布了《文物出口鉴定参考标准》,为文物外贸提供了法规依据。该标准的核心是设立了 “1795年界限” (即乾隆六十年),1795年以前的文物,原则上禁止出口。1795年以后的文物,经鉴定后原则上可以出口。此外,还有“1911年界限”(清代结束)作为辅助标准。同时,国家指定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四大口岸负责文物出口业务。
为确保文物收购与出口的顺利进行,国家建立了全国性的文物商店体系,全国共设立99家文物商店,其中54家拥有外销权。这些商店的核心任务,就是以极低的价格从民间收购文物,并组织出口。
出口规模数据(基于历史档案与研究):
高峰期: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持续约20年。
年均出口量:超过100万件。
累计出口总量:超过2000万件。
这一数据与海外中国文物总量估算高度吻合,从数量上印证了该渠道的主体地位。文物商店的货源是多方面的,包括考古发掘品(尤其是非珍贵文物)、民间征集、市场收购、群众主动上交与捐赠,以及特殊历史时期罚没的物资。收购价格由国家制定,价格低廉,一个明清时期的盘碗收购价仅3-5元人民币,一个明代永乐年间的花口大盘,收购价也不过3-7元。
出口并非精品挑选,而是规模化、批量化的处理:
瓷器:最大宗的出口品类。
书画:按“捆”计价、售卖。
玉器:按“斤”论价。
青铜器:按“尺寸”买卖。
这种交易方式,使得大量具有重要历史与艺术价值的文物,以“商品”的形式被捆绑、打包,以远低于其文化价值的价格流失海外。
到了80年代中后期,随着国家经济状况好转与社会观念变化,文物大量出口的负面影响日益受到关注。国家开始逐步收紧并最终叫停以创汇为目的的大规模文物外贸。然而,政策在执行中存在缓冲期,反而在80年代末引发了 “突击出口” 的浪潮。文物商店的成交额在此时期急剧飙升,从70年代的年均单店约45万元,跃升至80年代末的约800万元,90年代更是突破千万元大关。这从侧面反映了政策转变前夕,市场对文物的争夺与囤积。
“文物出口创汇”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国家在生存与发展压力面前做出的艰难抉择。它为国家换取了急需的外汇,支援了基础设施建设与民生改善,其历史贡献不应被全然否定。然而,从文化遗产保护的视角看,这无疑是一次规模空前的、不可逆的文化资源流失。它以一种合法、公开的形式,在二十余年间将数千万件文物推向海外,奠定了今天全球中国文物市场的基本盘,也使得后续的追索工作因“合法出口”的历史而变得异常复杂。理解这一渠道,是完整认识中国文物流失史的关键,也让我们对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发展间的平衡关系,有了更深刻的历史反思。
为了更清晰地呈现这四种路径的差异,以下从多个维度进行对比流失途径及主要历史时期。
古代及近代商贸交流,汉唐至明清:
合法贸易、礼品馈赠、文化交流
外销瓷、贸易银元、赠与海外的礼品
构成海外收藏基础,但非追索重点。
战争劫掠与殖民掠夺:
19世纪中叶-20世记中叶(1860, 1900, 1931-1945)
暴力性、非法性、系统性掠夺
圆明园兽首、汉白玉柱、《女史箴图》、被掠石窟造像
单件价值极高,道德追索焦点,但总量非最大。
盗掘与走私:
20世纪,尤其80-90年代为盛
犯罪性、隐蔽性、破坏性强
新近出土的青铜器、陶俑、被盗石窟佛首、馆藏书画
长期累积数量大,是当前司法与执法追索重点。
政策性出口创汇:
1950年-1980年(高峰70-80年代)
合法外贸、国家主导、规模巨大
按捆出口的书画、按斤出口的乐器、大量清至民国瓷器
数量占比最大,因历史合法性,追索最为复杂。
让流失文物回家,是国人长久以来的夙愿,也是国家维护文化主权、修复历史记忆的正当行为。近年来,中国在文物追索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前路依然漫长。
自1949年至今,通过多方努力,我国已成功促成超过15万件流失海外中国文物回归。党的十八大以来,回归进程明显加快,已成功实现59批次、超过2300件/套文物回归。文物回归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渠道,它们各有利弊,时常交叉使用。
依法追索:依据国际公约、双边协议或对方国内法,通过外交或司法途径要求返还。这是最符合国际法理、成本最低的理想方式。近年成功案例如:从美国追索西周丰邢叔簋;依据与意大利的双边协议,促成796件套文物返还;挪威收藏机构捐赠圆明园石柱。
公益捐赠:依靠海外华人华侨、国际友好人士、外国政府或机构的善意,无偿归还或捐赠文物。如何鸿燊捐赠圆明园马首、法国皮诺家族捐赠鼠首兔首、美国友人捐赠文物等。这是目前最常见的回归方式之一。
商业回购:通过参与拍卖或私人洽购,出资购回文物。如保利集团购回圆明园兽首。这种方式见效快,但存在变相承认非法交易合法性、推高文物价格、加重财政负担的弊端,多为权宜之计。
为系统推进追索工作,中国在国内法治与国际合作层面均加强了建设:
国内立法突破:2023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首次明确,对因被盗、非法出境等流失境外的文物,国家保留收回的权利,且该权利不受时效限制。这为永续追索提供了国内法上的“尚方宝剑”。
专门机构设立:2019年,国家文物局成立了 “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 ,负责统筹协调追索工作。
国际合作网络:中国已与27个国家(包括美国、意大利、澳大利亚、希腊、秘鲁等)签署了防止文物非法进出境及促进返还的双边协议或谅解备忘录,建立了稳定的政府间合作框架。
尽管成绩斐然,但相对于超过3000万件的流失总量,已回归的15万件,追索之路,道阻且长。
国际公约的局限性:追索所依据的主要国际公约(如1970年UNESCO公约、1995年UNIDROIT公约)存在无溯及力的致命弱点,无法约束公约生效前(尤其是殖民时期)的掠夺行为。且许多主要文物收藏国(如英国)并未加入1995年公约,不受其约束。
法律诉讼的困境:在外国法院提起诉讼,面临管辖权争议、举证困难(如需要完整的流传链条证据)、诉讼成本高昂等难题。“章公祖师肉身坐佛像”案在荷兰法院因诉讼主体资格问题被驳回,便是一例。
市场与“洗白”机制:成熟的国际艺术品市场为非法文物提供了伪造文件、多次转手以获取“合法”身份的“洗白”渠道,切断了其与原属国的联系,极大地增加了追索难度。
收藏机构的抵制:一些西方博物馆以“全人类共同遗产”、“保管研究需要”为由,或援引所谓 “博物馆职业道德准则” (如2002年《环球博物馆价值宣言》),拒绝归还。其背后是复杂的文化霸权与既得利益。
“出口创汇”文物的特殊困境:对于通过第四种途径流出的文物,其携带有特殊历史时期的“合法出口”证明,在国际法语境下追索依据最弱,更多只能依赖市场回购或友好捐赠。
让文物堂堂正正回家,需要智慧、耐心与持续的努力。未来可能深化的路径包括:
深化双边与区域合作:在现有与27国协议的基础上,继续扩大合作“朋友圈”,将双边协议做实做细,成为比多边公约更灵活有效的工具。
强化国内法治与涉外诉讼能力:利用新《文物保护法》的条款,探索在中国法院对涉及商业活动的持有中国流失文物的外国机构提起诉讼的可能性。培养精通国际法与艺术法的专业律师队伍。
加强证据研究与数字化建设:系统整理近代文物损失档案、考古报告、历史照片,利用3D建模、人工智能等技术进行文物溯源与比对(如天龙山佛首追索中的科技取证),构建强大的证据支撑体系。
推动国际道德与舆论共识:持续在国际场合发声,揭露殖民掠夺与非法贩运的历史与现实,将文物返还议题与全球文化正义、去殖民化思潮更紧密结合,形成道义压力。
鼓励多元社会力量参与:在政府主导下,规范并引导企业、基金会、民间组织以合理方式参与,形成合力。
中国文物流失海外的历史,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屈辱史、抗争史,也是一部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进行文化自省与身份重构的探索史。本文通过数据整合与历史分析表明,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是一个总量超过3000万件的庞大存在,其流失途径多元复合,远非“战争掠夺”一词可以概括。特别是20世纪中叶为经济创汇而进行的政策性文物出口,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了数量最为巨大的流出浪潮,这是我们在审视这段历史时必须直面的复杂现实。
面对如此巨量的流失文物,回归之路注定漫长。已回归的15万件文物,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开始,而非终点。近年来的成功案例与国内立法突破表明,中国正以更加成熟、自信和法治化的方式推进这项事业。然而,国际法律框架的缺陷、既得利益的阻挠以及历史遗留问题的复杂性,意味着追索将是几代人持之以恒的使命。
流失文物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当一个国家积贫积弱时,其文化遗产难免任人予取予求。当一个民族走向伟大复兴时,追索流失文物便成为重塑文化认同、彰显历史正义的必然要求。这项工作不仅关乎具体的器物回归,更关乎对一段不平等的全球历史进行伦理修正,关乎构建一个更加公正、平等的全球文化遗产治理新秩序。让文物回家,就是让历史归于完整,让文明的故事能够被它的创造者子孙继续讲述。这条路,我们必须坚定地走下去。
文|孔达达 研究员
免责声明:市场有风险,选择需谨慎!此文仅供参考,不作买卖依据。